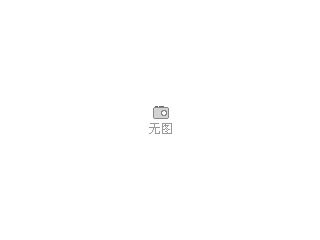您所能承受的总是比您想像的要多的文字
/NianNian1睡前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NianNian,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的读者,您曾经为我写过一篇文章
这句话很快使我想起了关于她的故事
去年,由于关系破裂,她陷入了人生低谷
她每天都在家里关门,没有外出,也没有与朋友互动
饭后,我在大山乡政府窗明几亮的接待室里翻阅着有关材料
材料中我了解到大山乡党委、政府是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我大体了解到大山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全乡经济总收入三千二百多万元,两万多人口中,人均经济纯收入达一千多元,人均产粮三百六十多公斤
这些数字,在边、山、少、穷地区难免让人眼前一亮
李书记告诉我,近年来,大山乡党委、政府立足乡情,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建立了以烤烟、甘蔗、畜牧业为主的产业群,产业发展收到良好效益
辖区内大山村年内仅烤烟就冒出了二十余户万元户;昔日被称为“哑巴寨”的牛火塘自然村,仅烤烟收入人年均就达四千元左右
群众有钱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时间随短,却仍旧逝去;年龄虽长,却也瓜代急遽
咱们荡游在这亦长亦短的功夫里,也应充溢运用,切勿使本人丢失个中
35、父爱同母爱一样的无私,他不求回报;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仅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
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十多年的中原,离开了这块皇天厚土,离开了那些同甘共苦的兄弟们
上车了,我的落脚点在两节车厢的对接处,于是哐噹巨响声伴随我一直到了四川成都
看看我的行头你就知道我像一个逃荒的,所有的书和破行李卷装在一个蛇皮口袋里,我就坐在行李上
列车开始鸣笛出发了,但是我的前方却很模糊,眼前不断闪过的是棉花,芝麻,玉米杆以及中原上所有的景物将从此消失在我的视野里,而云南在我脑海里也已经像印了水的墨迹,很淡,很淡
多年来我一直靠着书信残存着点滴高原的印象,那些书信就在那个包里,足足的一尺高,高原平原的描述多年来全装在信笺上的墨迹里了,小时候的种种事情只是零星地泛在脑海里,我把头埋在双腿间,十多年终于把我完全改变成了一个北方人
李斯年少时,除了文前提到的可能看见了顽强无垠的冰草,还看到了两种地位不同的老鼠:厕所的老鼠和仓库的老鼠,厕所的老鼠骨瘦如柴缩头缩脑,仓库里的老鼠硕胖高傲目空一切,同为老鼠为什么有天壤之别?李斯很快联想到:即便是一个白痴,把他放在王宫贵族的行列,也是显贵无比;再有本领与素质,如果没有好好发挥或者没有发挥的条件,也注定要屈辱一生
他甚至直接这样说了:“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与贫困”
这些都是早年的李斯欲望的觉醒
按照叔本华的理论人之欲望有活下来的欲望,爱和被爱的欲望,控制的欲望、攻击的欲望、催毁的欲望.......出身贫困的李斯首先想到的是活下来,然后才是其它
上世纪八十岁月中叶,我在崇麓教书,偶尔,与王如麟到建党家里去,建党的母亲就会把从山里采来的映山红花荡涤纯洁,与果儿搅在一道,煎出香馥馥的花蛋来,或把洗净的映山红与白面和在一道,做出甘甜的花饼来
咱们特殊爱好吃花蛋、花饼,每当建党的母亲把冒着热气的花蛋、花饼端上去时,咱们城市吃个净尽,那种香醇的滋味于今仍深留在我的回顾中
那里有拥挤着打饭的我们
还记得那个长草的操场吗?那里有大喊着让小区楼道声控灯亮满的我们
还记得那个栅栏吗?那下面有为少走路钻过去的我们
还记得那条巷子吗?巷子里奔跑着欢笑着的我们
记得当时,“汪国真现象”曾让国内文学界所谓准诗人和理论人士唯心的定位为“伪诗”或者“非诗”,并且在国内有威信的报刊上屡屡撰文,狠狠批评,甚至强烈要求立即“封杀”汪诗的发表和出版,重振诗坛之新风,弘扬诗国之正气,一些人还把他归为三流诗人,不留情面的说读汪国真的诗歌就是诗人的不幸,就是走向了一条诗歌的死胡同
还说汪诗只不过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精髓断章取义之后的重新组合等等
但这种批判的声音在国内数亿万热爱和拥护“汪诗”的读者群中哔竟是微弱的
文学既是人学,它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体
尽管汪国真和当代诗歌潮流走着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毋庸置疑,正是这种独辟捷径,自成一派,清新隽永的诗歌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吹进了一股温暖的春风
至少让世人明白,“读懂”与“读不懂”的诗歌决定着读者的选择与取舍,也决定着诗坛的活跃和沉寂
汪国真的诗歌正是在中国的诗歌在读者中很“读不懂”而较有争议的趋势下以其横溢的艺术才华,独特的创作风格,清新贴切的诗风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从中脱颖而出,因此,可以说是诗歌成全了汪国真,时代捧红了汪国真
汪国真对整整那一代青年们的影响也是有益而且深远的
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同意第二种说法,历史上,人们对麻疯病的恐惧心理,让人们宁可相信黑太阳,而不愿意承认历史上的核桃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