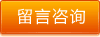我和夏雨对着坐,很小却很温馨的一个小餐厅
很明亮的灯光,放着一些轻柔的音乐
笑完后她羞涩的低下头,我可以贪婪的打量她今天的打扮
浅绿色的体恤,洗得很白却很干净的牛仔裤,白色运动鞋,镶着浅蓝色的边
那件蓝格子的外套被她很巧妙的围在了腰上,有裙子的风彩,却更多一些天真无邪的野性
她说这是痞子蔡说的“格格bule”,要系在腰上当裙子穿
很完美的曲线,小巧而精致,活泼而不乏活力,有很轻很柔声音,却有开朗的性格和野性的笑
她说她是双子星座,所以注定有些复杂的东西纠缠在一起
写这首诗时,居于昆仑山下一个叫:格尔木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飘扬着蒙古族人祷求吉祥的经幡和棕黄土地上屹立起的银色铁塔,看到了原始与现代的共融与和谐,因此,在这里让我完全张扬开了,一切都不需要假装,包括所谓的“活着”竟是如此的朴实,不需要任何的修饰
心里沉淀着某种真实,便会顿悟:皮肤被阳光灼伤后的颤悚还有惊喜;读到胡杨亲近湛蓝天空的祥和还有坚强;看到久居北漠的朋友,那样深情的爱着这片贫脊的土地,一辈子不愿离开的痴情
我知道,这首诗真的不是为自己写的
许多个夜里,我仿佛梦到自己又在拨融风雪,用北方的石头敲击着北方汉子的心坎,清脆而深远
醒来后,发现是梦在向西,继续向西
拨给北京某杂志社大编辑的电话通了,“嘟——嘟——”呻吟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电话那头有人应答
“喂!你好!”“您好!”“格尔木,片子和文字已经做完,准备择日寄出
”“哇!格尔木,我去过,那个地方实在太恐怖了
”没等我问,编辑已将曾去往北漠采风所获的感受浓缩成了干疤疤的两个字“恐怖”,一点也不勉强地在传递给我
此刻,像是在午夜,我的眼睛瞅到了窗外悬挂的一只咸鱼,等待风干
随后,伸手去抚摸一下咸鱼的味道,而没有说一声:再见,就把电话丢下了
不知是在为自己的怜而疼痛,还是在为这编辑对待客观事物认识肤浅而悲哀
后来我还是决定将文稿及相关图片寄去
我想:至少告诉这位编辑,生命中其实还有一种颜色,一直在被我们忽视或是误解
我还想告诉他;在这里繁衍着一种真实与宽容,还有我们不曾真的用心去听懂的咒语,浓缩了也只有两个字——美好
我在磨坊里,整日整夜将房里四处堆满祈求赦免的每一只茫然的眼睛——每一粒黑麦,磨成流动的白色浆液
当一个“折”叫醒了古老磨房里每一片砖瓦和沉静时,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发动机,高速旋转的齿轮,一张“现代”的王牌,的确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披上了坚硬的外壳,但同时也让我们由此变得冷漠了,但指与指的隙缝间,是否淌出的仍然是粮食呢?在城市间游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发问和回答,拒绝,逃避,再去发问
站在夜幕里,我渴望看到一粒黑麦——一只凸显的眼睛
“狗子”,我忽然听到这样一声
这声音温婉、可亲,仿佛一阵凉风拂我
这虽不是母亲叫我,但我想起母亲了,想起母亲为了我一生幸福,替我取这个贱名的初衷
也就真正感到先前羞愧丑名,是怎样一种无知和幼稚,而远在他乡未尽好孝心才是自己最应感到愧疚的
同业者一人,伙伴杨氏,曰天鹏者
那壶辛酸的酒让他喝了一辈子,在他身上那是一块不许去显现的长久的悲痛,以至一辈子都成了一块缺点
回顾其时的七月流火,就像我对生存的关切,对将来无穷向往着
这是不祥之兆
我总是企图把自己挂在芒刺尖儿上,享受它赐予的孤独和疼痛
透过人们浮华,水波一样湿漉漉的眼睛,看道旁的野蔷薇怎样一蓬蓬地盛开,蓊郁的香混合着炙热阳光的烘烤气息
然后残忍地期待它们最终的凋落,在山羊绵软的唇下连着草根化为乌有
就像一幕布景华丽的歌剧,在最高亢的时候也就接近落幕,观众不安地攥紧了手包,唤回满地乱跑的孩子,性急的已经走到门边,回头张望结果
《后会无期》经典台词,后会无期经典台词大全 9、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分利弊
《后会无期》
雨声淅滴答沥,迷阴暗蒙
透过雨帘,那未眠的街灯,仍旧闪耀在酣睡的天穹极端
雨声渐响,我的思路也随着飘了起来
凝思中,犹如惟有功夫老翁在水光闪闪的路上,徜徉而行
、人生皆有遗憾,有遗憾才是如实的人生
那种看不见人生遗憾的人,大概是童稚的,大概是麻痹的,大概是自欺的
恰是在缺点和遗憾中,在对缺点的宽大和对遗憾的接收中,人快乐地生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