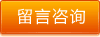生存是部分镜子,质本纯洁的精神里追赶着幼年功夫放荡而浓愁的理想
曲折漂迫里探求着人命的意旨
睡梦中下起了雪,鸦雀无声,遽然发觉到一阵和缓,蜷曲着身材反抗着犹如不甘心的格式,摩挲着被角却创造不过睡久了窝存的一丝和缓,冷气袭人,本质里感触着孤独与凄冷
身材积聚的病痛如泣如诉如怨如怒的在身材里哀号,无穷的给予里寒夜变的惨白而而飘荡,泪水沾湿了靠襟,良辰美景如画的晚上备受煎熬
对于水,我一直有一种诲莫如深的敬畏,关于对水的回忆,我总是有一种几近苍白的无奈
人的出生与人的宿命一般,注定是无法逃避和选择的,这就如同有的人生来就享受丰奢,而有的人诞生就意味着忍受贫苦的折磨
尽管在享受丰奢或忍受折磨的人心中,也许并不是丰奢和折磨
如果说水是一种幸福的话,我的出生地决定了我无法抵达幸福的边缘
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距离可以被称之为河的最近的水——黑河,也有百余里,就这距离之于一个偏寂贫瘠的小村的我而言,二十岁以前,不啻于万里之遥
因此,水注定会成为我的敬畏也注定会成为我记忆的苍白
最初对水的认识是环绕村子而过的那条扭扭曲曲的小溪
每年夏天,山雨过后,祁连山海潮坝中涌下的水肆意地绕过村子,流向我不知道方位的去处
我和我的伙伴们在那样的夏天里便欢乐成鱼的模样,赤裸地在深不及膝的水中畅游
天,那也叫畅游吗?那不过如戈壁滩一些焦渴的花刺柴在一场雨后短暂贪婪的吸吮而已! 除此之外,对于水的认识,就是村子里那两汪干渴的鱼眼般的涝池,那是维系全村人一代代支撑着活下来的生命之源——我对水的敬畏绝对缘于那两潭死水,尽管在干渴的夏日里涝池里共生的鱼、蛙及各色不知名的水虫把涝池的水搅得浑浊如阴郁的天,它在村人的心中依然上天般的神圣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幼时村人每年必定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祭奠坝神——也许是水神——的庄严与神圣,以及闪烁在我的父辈们脸上的虔诚与恭敬
如此一种对水的直观认知,我又能对江、河、湖、海能达到何种逼近的想象呢? 上学时,老师讲到黄河、长江,讲到大海,我尽可能让自己幼稚的想象与联想的翅膀竭力腾飞,也只能把黄河长江想成海潮坝的某个山口,把海想成祁连山般的高大
由于此,对于诸如波涛汹涌,碧波荡漾,水流湍急之类的词语在我脑海中实在是艰涩模糊、难以理解的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或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把江河湖海想象成山的模样,即使真有,我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绝对能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书中听到关于水的许多声音:屈子临汩罗而泣,东坡登赤壁而叹,霸王退乌江而吼
10、每次老师说,请把和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到讲台上,我就很想把自己放到讲台上
一团喧闹之后咱们再次动身
这是一条规旅环线,路过麻羊之乡悦来镇、张道陵布道的鹤鸣山道观、共享小镇斜源古镇等得意区
白车穿行于苍山之间,又有绿水相伴;车内清歌曼妙,窗外得意如画,自由自在
喜欢你的暖心文字,让人很是期许你所说的承诺
缘起,我愿陪你花开,缘散,我愿伴你花落
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待繁华落幕,待经年流尽,携手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