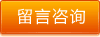“恩!是你?”我一听是升哥儿的声响
遽然间气氛就像冻结一律,定在了何处
有点不领会该说什么,结果仍旧随意问了句:“如何?有事吗?”
生在河泊,漂在海面的菱蓬,有家菱野菱两种
家菱个大角软,靠人为载培繁衍;野菱个小角尖,天然成长而成
家菱中再有红菱、元宝菱、环菱三个种类,以元宝菱产量最高,品德最好
在我入学此后,熟稻只有一割,那巨细的水田内,就畈畈有鸭游
海笑来找过,黄蓓佳来寻过,就连老外们也来感受过呢
自我,写作就成为了无效的劳作,只能跟着别人走,无法确立个人
另外,我个人觉得,地域对写作实在重要的,也是一个有效的支撑,它可以在很多时候让人可以开采出更多的关于生存、风俗乃至灵魂的东西
我相信某些东西,比如品质、命运、习气和趣味是与生俱来的,福楼拜一生就写他生活的那个小镇内外,何尝不令人高山仰之呢?与山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难,难得俺浑身冒汗,感谢与山兄
阿贝尔:问献平:写了这么多,想没想过完成之后又怎样? 答阿贝尔:阿兄这一问,倒是叫俺想起了什么,其实写东西,永远都在完成,也都在诞生,我们做的,只是一直在完成,在到达
没有一个文章都是开始,而每一个开始都不是有终结的
写了这么多,其实还在路上,想象和预期的终点遥遥无期,我不是一个能写的人,也不具备相应的才略,更无称霸天下的雄心,只是一个小人物,小蚂蚁,愿意在自己的路上走
总感觉自己既像一个落魄者,又像一个背着自己旅行的人,文字不过是闲暇时的一种消遣,它所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狭窄而微不足道的安慰,除此之外,都让纷繁而忧伤的生活和种种遭际代替了
阿贝是有思想的,向你致敬! 柯英问:1、处于河西走廊围墙外面的你,一直是以什么身份观察西北?A、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