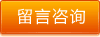但我还是重视的,不打无准备之仗
我现在无事可干,他们把我圈在这里,有不掏钱的饭供应着,有武警荷实弹的看护,他们分配给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专门对付他们
最后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我喜欢喝可乐加冰,但这儿无法买到
这儿卖的最多的是兑了水的豆浆
有一次我在封闭的豆浆里面找出一只苍蝇
我没有和别人说,因为我说了也没人相信
我不打算阐明自己的观点,或叫辩解
其实,我现在连解释就显得多余,自己实在是不够格
我只觉得作家和朋友们都把我想得太理想化,或妄自尊大,或疯狂
——这些需要足够的能量和天性,而我并不具备这些
就是有这本领了,我却也无此天性
说真的,你不难发现,我并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也无理想主义的幻想
我还没有能力超越到虚无,悲观和绝望是需要更大的勇气,也需要更大的能耐;那是需要达到衣食无忧,那是需要绝对的自由,这才是疯狂的事情
而我只是一只卑微的小虫,是一个失望的爱好美术的人,一个自小就爱好美术的人
我也只剩下这个可怜的追求,艺术就成了我的逃难所,或与现实的对抗,是我的精神支柱
从多年来看,美术对我的确是个好东西
知道这样的情况后,母亲和小姨妈时常去看她
冬天,母亲和父亲一起去给大姨拾些柴禾,劈开,放在灶火旁边
播种和收割时候,也去帮忙干活
大姨总说我们一家对她好,有一次,偷偷对我说,她攒了5000多块钱,好像三表嫂知道,给她要了几次
我叮嘱大姨,这钱谁也不能给,留着自己用
大姨还说,早年间,没信基督之前,有算命的对她说,到她78岁那年就没了
我听了,很伤感,看着她鬓间的白发,忽然觉得了悲伤
70多年了,这一个人,走过了她人生的大半时光,膝下6个子女,一个远在他乡,两个壮年夭折,现在只剩下两个名副其实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了,孙子孙女个个长大,也有了一个重孙子
但是,她好像没感觉到幸福,总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每次见到,大姨总要和我说很多话,叫我乳名
说着说着,眼泪汪汪地哭起来
有几次,从兜里掏出我这些年断断续续给她的钱,硬往我手里塞,我急忙跑开
每次打电话回家,也常询问大姨的近况,嘱咐母亲多去看看,没事了就把她接过来住几天
我知道,大姨老了,母亲也一把年纪了,两个同胞姐妹,风雨大半生,老了,晚上,躺在同一面炕上,说一些往事、家事和心事,尽管她们一定都会很伤感,但那种情景应当是温暖和亲切的
司机告诉我们:阿尔金山上的雪融水,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每到正午,水流就会加大,这些石头就在水流的反复推动中,一寸寸前进
若要遇到山洪,那石头与石头的碰撞声,就有了鼓角争鸣的山崩地裂,有了千军万马的厮杀
那种气势,的确令人胆寒
但袒露在我面前的流石沟,显得格外平静,像一位羞涩的牧羊女,她的鞭子,这会儿不会抽打在你的身上
她是用悠远、深情的蒙古长调来迎接远方的客人
倒是我们这些唐突的访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我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们也不能惊扰她的宁静
车道就在卵石排列的河床上,越野车不进则退,不能够停下来
我们又多了一份遗憾
一辆行进在大河上的越野车,似乎像一只飞翔的黑鹰;而我们,则在它宽阔的鹰背上
闭上眼睛,流石沟连绵不断的卵石,像天堂飘拂的风铃,走失的风铃,让这块大地更加生动和深刻
你会想到,这群不恋天堂的女儿,如何就选择了雪山脚下的这片土地,选择了这块世外桃源
我一直想越野车要能够停下来,拍一张与她们的合影多好
这是一块看不够的石头世界啊,自然赋予她们的灵性,我们只能留在心里了
流石沟像一个童话的憩园
我想,你要是站在鹅卵石上,南眺白雪皑皑的阿尔金山,北观枯草连天的草甸子,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地上的行吟诗人,一个汲纳了天籁的灵性的野生植物
你就生长在卵石上,你的根茎就伸展在雪融水中
你会在一瞬间长大,甚至高过了雪山
你会有着炫目的金色彩,有着白云一样的梦幻
这时候,你张开翅膀,满河沟的鹅卵石,都会跟着你飞翔